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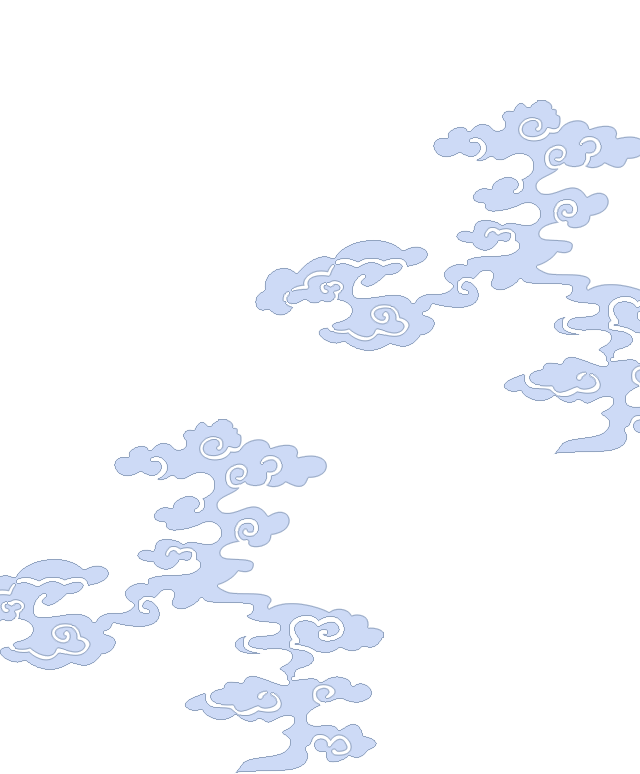
古人对画稿早有定义,各言其意。元代夏文彦《图绘宝鉴》说“古人画稿谓之粉本”。其方法有二:一是用针按画稿墨线(轮廓线)密刺小孔,把白垩粉或高领土粉之类扑打入纸、或者用透墨法印制,使白土粉或墨点透在纸、绢和壁上,然后依粉点或墨点作画;二是在画稿反面涂以白垩、高岭土之类,用簪钗、竹针等沿正面造型轮廓线轻划描印于纸、绢或壁上,然后依粉落墨或钩线着色,此法犹如现今常用的复写纸原理。
此次展出敦煌莫高窟壁画粉本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与敦煌壁画造像等大,直接在敦煌壁画上原大勾勒摹写。
(二)每一幅粉本造像的各部位颜色用汉字(繁体字、异体字)标注,非常完整细致,如服饰、璎珞、五官等。与张大千其他粉本有较大不同,张大千目前所见粉本颜色标注文字很简单,多为主要部位标有颜色,如服饰部位等。这些汉字标注颜色的方法是为日后创作上色做准备。
(三)粉本上编号为张大千为石窟编号,“C”字打头,如C二七九,并在编号后标注造像位置,如C二七九前右观,“观”是佛造像名称的缩写,如观世音菩萨。
(四)以墨线轻松勾勒为原初稿,即第一手粉本稿,未有后期加工。故最接近原作。
(五)所用纸张多为拼接,节约意识强,为解放前手工竹浆纸,偏黄,较薄,利于复制拷贝。
(六)制作粉本时,是将纸直接用图钉或其他钉子钉在壁画上,纸用煤油打湿,等纸略干用墨线勾描。(现在纸的上方都留有钉眼和下部积有油渍)
(七)这批粉本都为佚名,拆封时,每一幅都用民国年间(1944-1945年)的《中央日报》包裹,应该有六十余年没有拆封,且原样保存并留有沙子,纸张碎裂易断。
(八)这批粉本时间在1944年之前所绘。时间与张大千“敦煌时期”(1941-1943年)相近。因为1944年敦煌国立文物研究所成立之后这种破坏壁画的画稿方式是被禁止的。详见何鸿、何如珍主编《穿越敦煌-美丽的粉本》,西泠印社出版社,2015年。
古人对画稿早有定义,各言其意。元代夏文彦《图绘宝鉴》说“古人画稿谓之粉本”。其方法有二:一是用针按画稿墨线(轮廓线)密刺小孔,把白垩粉或高领土粉之类扑打入纸、或者用透墨法印制,使白土粉或墨点透在纸、绢和壁上,然后依粉点或墨点作画;二是在画稿反面涂以白垩、高岭土之类,用簪钗、竹针等沿正面造型轮廓线轻划描印于纸、绢或壁上,然后依粉落墨或钩线着色,此法犹如现今常用的复写纸原理。
此次展出敦煌莫高窟壁画粉本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与敦煌壁画造像等大,直接在敦煌壁画上原大勾勒摹写。
(二)每一幅粉本造像的各部位颜色用汉字(繁体字、异体字)标注,非常完整细致,如服饰、璎珞、五官等。与张大千其他粉本有较大不同,张大千目前所见粉本颜色标注文字很简单,多为主要部位标有颜色,如服饰部位等。这些汉字标注颜色的方法是为日后创作上色做准备。
(三)粉本上编号为张大千为石窟编号,“C”字打头,如C二七九,并在编号后标注造像位置,如C二七九前右观,“观”是佛造像名称的缩写,如观世音菩萨。
(四)以墨线轻松勾勒为原初稿,即第一手粉本稿,未有后期加工。故最接近原作。
(五)所用纸张多为拼接,节约意识强,为解放前手工竹浆纸,偏黄,较薄,利于复制拷贝。
(六)制作粉本时,是将纸直接用图钉或其他钉子钉在壁画上,纸用煤油打湿,等纸略干用墨线勾描。(现在纸的上方都留有钉眼和下部积有油渍)
(七)这批粉本都为佚名,拆封时,每一幅都用民国年间(1944-1945年)的《中央日报》包裹,应该有六十余年没有拆封,且原样保存并留有沙子,纸张碎裂易断。
(八)这批粉本时间在1944年之前所绘。时间与张大千“敦煌时期”(1941-1943年)相近。因为1944年敦煌国立文物研究所成立之后这种破坏壁画的画稿方式是被禁止的。详见何鸿、何如珍主编《穿越敦煌-美丽的粉本》,西泠印社出版社,2015年。